

下文为《景观的文化遗产化——观光旅行、博览会、博物馆的19-20世纪》,[日]丸山泰明著,余玮译。摘自集刊《遗产(第8辑)》,周永明任主编,王晓葵任执行主编。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不仅是日本,世界各国都开始形成一种法制框架,即把在人们生活地域内所创制出的景观作为文化遗产来保护。与在此之前的,把建筑物之类的事物指定为一个个文化遗产进行登录、保护的做法有所不同,这是将单个的建筑物集合起来,连带周围的环境来做一体式的保护。诸如农山渔村的家屋,都市的街区,梯田、矿山、采石场等与生业、产业相关之类目,被包含在“景观”范围内的人的生活行为实属多样。但这些“景观”均被嵌入了一个共同的视觉性要素,即是“离远了看”。也就是说不仅仅是“看”,重要的是“离远了”来“看”,它内含这样一种视觉性:从离保护对象稍稍远一些的地方(这个距离视保护对象而定,十几米远至数千米远不等)望去,将此时所切取的空间重新进行一体式保护。
日本是在2005年修正的《文化财保护法》中新设了“文化景观”保护制度。其中对“文化景观”进行了如下定义:“在基于地域内人们的生活和生业以及该地风土而形成的景观地中,对于理解本国国民的生活以及生业来说的不可欠缺之物。”(第2条第1项第5号)这一制度与2004年颁布的“以促进本国的都市、农山渔村等地形成良好景观”(第1条)为目的的《景观法》有着密切关联。此外,这一基于修正后的《文化财保护法》所设的“文化景观”保护制度还与当前渴望“美丽的景观”并对生活空间做出改变的社会状况有所关联。
将某一地域的人们在生活和工作中所形成的空间一体化地视作“博物馆”的制度,也在博物馆领域中不断地被调试。比如,2007年日本文部科学省生涯学习政策局设立了“关于将来博物馆理想状态之检讨合作者组织”,该组织在同年6月提交了一份对《博物馆法》进行修正的报告。这份名为“关于新时代的博物馆制度的理想状态”的报告书里进行了这样的提案:“把古街区、产业遗产、历史建筑物群作为博物馆资料,并把涵括了这些资料的一定范围内的区域作为‘museum’来进行构建的地域举措,视作在对博物馆的资料进行‘收集、保管’,在后述的调查研究活动等等必要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应开放途径使其能够被以博物馆之名加以登录。”虽然在文中并未明确使用“景观”一词,但这种构想已初见雏形。
促使日本加快对作为文化遗产的“景观”进行保护的一大要因是,日本在1992年所批准加入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里出现了“文化景观”这一概念。“文化景观”这一概念是在1992年12月美国圣塔菲召开的第16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上被决定引入使用的。这一概念的内部又被进一步分类成:(1)庭园、公园之类被精心设计的景观;(2)有机进化而来的景观;(3)诸如新西兰毛利族的圣地、汤加里罗国家公园那样——自然要素丰富的,宗教的、艺术的、文化的景观。接着,第(2)类又被进一步分为:遗留景观,如柬埔寨的吴哥窟遗址;以及持续景观,如菲律宾的科迪勒拉的梯田。依照日本的《文化财保护法》,第(1)、(3)类相当于“名胜”,第(2)类中的遗留景观与“史迹”相当,只有第(2)类中的持续景观相当于“文化景观”。芒果体育手机版在日本的世界遗产中,被登录在“文化景观”名录下的有“纪伊山地的灵场和参拜道”(2004年登录)与“石见银山遗及其文化的景观”(2007年登录)。
围绕着近年来的上述动向,本文旨在通过历史性的回溯究明,为何要把景观作为文化遗产来保护这一问题。
关于“景观”的文化遗产化,除了文化遗产学、博物馆学,人文地理学、建筑史城市史等研究领域亦采用各自的研究方法对其进行探讨。笔者在本文则有意依托自己的专业,也即民俗学的立场去展开研究。不过事先要说明的是,在“景观”中,一直被视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的农村、山村、海村之类的相对于都市而言的地方的“景观”,并非本文的考察中心。
日本民俗学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就对民俗及其文化遗产化的问题进行了批判性研究,并由此形成了一大研究倾向——只聚焦于日本的《文化财保护法》展开讨论。对把民俗作为文化财进行保护的《文化财保护法》的内在思想、意识形态性,保守势力对《文化财保护法》的制定与修正进行的介入,文化财指定给对象带来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检讨。这类检讨的成果虽使我们获益匪浅,但也有缺失之处。首先,《文化财保护法》这部法律一直被置于议论的中心,导致研究的问题意识被局限于日本国内而欠缺国际视野。此外,由于作为文化遗产保护机构的博物馆被忽视或者说被轻视,相关研究缺失把日本的《文化财保护法》置于文化遗产保护这一整体性历史中去把握的视点。为此,本文将试图加入这些视点来展开讨论。
在神奈川大学21世纪COE项目“以人类文化研究为目的的非文字资料的体系化”中,“景观”被定位为非文字资料的一种。该项目启动时,被置于研究体制下的第3班的研究题目是“环境和景观的资料化与体系化”。而研究题目为“文化信息传布的新技术的开发”的第4班,则是以探讨非文字资料如何在博物馆内进行保存、活用的方法,以及培养在博物馆中专门从事保存、活用工作的高级学艺员为目的。如此看来,把作为非文字资料的“景观”进行资料化、体系化,并探讨如何对其进行信息传布的课题,理应是与同时期的“景观”文化遗产化的动向密切结合着的,换句话说,如果意识到了研究的“同时代”意义,应当是要积极地将二者进行结合的。然而,在本项目实施的五年间,一直未产生与“景观”的文化遗产化的动向结合起来的课题。为此,本文在对“景观”的文化遗产化的历史过程进行考察之时,也期望能对此课题有所贡献。
历史地来看,把“景观”作为文化遗产来保护的这一尝试,最初呈现为野外博物馆这一形态。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瑞典、丹麦、挪威、芬兰等北欧诸国,相继成立了民俗博物馆。而这些民俗博物馆又以野外博物馆或是和野外博物馆并设在一起的形式呈现。
1873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设立了斯堪的纳维亚民族志收藏(Scandinavia Ethnographic Collection,也即今日的北方民族博物馆)的阿图尔·哈则流士(Artur Hazelius),1891年在瑞典设立了斯堪森(Skansen)野外博物馆。翌年1892年,乔治·卡尔林(Georg Karlin)在瑞士南部的隆德(Lund)市设立了库尔图伦(Kulturen)文化史博物馆。挪威在首都奥斯陆(Oslo)的郊外比格迪(Bygdøy)半岛上设立挪威民俗博物馆,并于1901年对外公开。此外,利勒哈默尔(Lillehammer)市在1904年购入了安德斯·桑德维格(Anders Sandvig)的收藏,在市郊外的山坡上开设了麦豪根(Maihaugen)博物馆并对外公开。丹麦是在1901年,由伯恩哈德·奥尔森(Bernhard Olsen)在首都哥本哈根的郊外开设了野外博物馆(Frilandsmuseet)。而芬兰在首都赫尔辛基的郊外设立塞里(Seurasaari)野外博物馆是1909年的事了。

斯堪森(Skansen)的房屋与农场。斯堪森野外博物馆馆区内包含从瑞典全国的约160间房屋和农家庭院,还有斯堪的纳维亚特有动物品种。(图源)
这些野外博物馆通过移筑各个地方上的家屋,以及再现家屋周围的农场和牧场,来对各个地方上的“景观”进行重现。家屋的内部放置着生活道具,并由穿着民俗服装的工作人员做出在此生活与劳动的样子来营造氛围,到了周末或假期则会进行一些民俗艺能的表演。而夏至或是圣诞节之时,会举办每年的例行仪式活动供参观者体验。如此,“景观”的文化遗产化最初是以在野外博物馆里再现的形式开始的。
一般说来,1891年由哈则流士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开设的斯堪森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野外博物馆。并且以斯堪森为模板的展示手法从北欧扩展至全欧洲,再向世界传播开去。
但这种将野外博物馆的展示手法归于哈则流士的想法,受到了丹麦民族学者皮亚尼·斯托克伦(Bjarne Stoklund)的批判,他认为这是一种“哈则流士神话”,并将之解体。依据斯托克伦的说法,实际上这一展示手法并非哈则流士独创,在设立斯堪森的1891年以前的万国博览会上就已被普遍使用。
“哈则流士神话”里的表述,是说哈则流士在1878年召开的巴黎万国博览会上尝试了新的展示手法。在博览会上,他再现了小屋内部的场景,并且布置了室内装饰和穿着民俗服装的人偶。此外,还再现了拉普兰(Lapland)的山景,同时把萨米人(Sami)的人偶和驯鹿、帐篷一并展示出来。虽然参观者并不能直接进入这个立体模型,只能在低一级处观望,但这一展示手法直到1878年巴黎万国博览会之前并未出现过,也因此这一展示经验启发了1891年斯堪森这一新式博物馆的成立。
然而,存在一个与哈则流士完全不同的人偶制作者卡尔·奥古斯特·塞德尔曼(Karl August Söderman),他在1867年巴黎万国博览会、1873年维也纳万国博览会、1876年费城万国博览会上都做了这一类的展示。而与哈则流士在1878年巴黎万国博览会上所设的萨米人相同的展示,早在两年前的费城万国博览会上就已出现过。
加之,在屋内再现驯鹿,并配有身着民俗衣装的人偶展示也不是瑞典地区的特有之物。在1867年的巴黎万国博览会上,法国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其他15个欧洲国家,就都把身着民俗衣装的人偶送来展示了。
另外,在博览会主会场外部的建筑物内进行展示这一做法,在1867年的巴黎万国博览会就已开始。世界最初的万国博览会,也即1851年的伦敦万国博览会,是把所有的展示物都收在“水晶宫”这一巨大的建筑物之中。这样只在建筑物中进行展示的手法虽持续了一阵子,但从1867年的巴黎万国博览会开始,各国就也在建筑物的外部建设展馆了。在这些展馆内,有宗主国携带着殖民地的住民们一同来参展,也有欧洲各国对自己国家、自己民族的生活进行展示。罗马尼亚建起了小教会,挪威则把泰勒马克(Telemark)地方上的带有阁楼的小屋建了起来。俄罗斯把建筑工人带来建造了带有马厩的农家庭院,并在其中展示俄罗斯的民俗文化和物品。澳大利亚则建造了7个地方上的房屋,这也几乎成了一个小型的野外博物馆。
而为了万国博览会收集而来的展示物,后来都成了各国民俗博物馆的收藏品。比如,丹麦民俗博物馆就收藏了1879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美术·产业博览会时收集而来的展品。创设了丹麦民俗博物馆的伯恩哈德·奥尔森在1920年出版的《百科事典》的野外博物馆这一项中写道:“万国博览会是野外博物馆的起源。”就这样,皮亚尼·斯托克伦参照对以往的博览会史和博物馆史的研究,把在野外博物馆的历史叙述中一直受到忽视的万国博览会的这一部分内容给补上了。
迄今为止,关于万国博览会,常为人论及的是在会上所进行的人种展示,也即宗主国把自己殖民地上的住民带来参展的事。日本研究者也对欧洲各国和美国在博览会上对殖民地住民进行展示一事进行了批判。但欧洲各国在万国博览会场上对自己国家的传统生活方式进行再现和展示这一事,却几乎未受到任何追究。
在此要注意的是,从万国博览会到野外博物馆的这一支脉并不仅仅意味着万国博览会只是在推动民俗博物馆展示手法的成熟以及资料收集方面起到了效用。万国博览会是一个参会各国(举办国自不必说了)通过展示最新的科学、技术、产品,或是具有异国情调、传统的物品,来回应人们想见稀有之物的欲望,并借此夸示国力,展露本国形象的一个场所。而承袭这一系谱的民俗博物馆,则意味着国家在自我表象化过程中,于19世纪后期产生出了一类视觉体验及一种认知的体系。

野外博物馆被设立的时期,也是北欧重设国境线、各国疆界被划定的时期。19世纪中期的北欧,高扬着瑞典、丹麦和挪威三国联合对抗列强的泛斯堪的纳维亚主义运动。在这一运动受挫后,各国则以民族国家的形式分别成型。丹麦在1864年与普鲁士和奥地利的联合军作战的第二次石勒苏益格(Schleswig)战争中落败后,被普鲁士夺去了位于日德兰半岛根部的石勒苏益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石勒苏益格的北部地区被归还)。而在瑞典支配下的挪威获得独立是在1905年,芬兰从俄国独立出来则是在1917年。民俗博物馆就是各国走向近代民族国家的这一民族主义的时代境况下的产物。伴随着近代化与工业化消失而去的昔日生活被视为表现国民身份认同的传统,对此进行研究的民俗学因之兴起,博物馆也对此进行收集、保存、展示。
因此,野外博物馆的设立和其中对地方上的“景观”所做出的选择,均有民族主义的影响。因而,野外博物馆所选的是那些被认为是代表了这个国家的地方上的“景观”:在瑞典是达拉纳(Dalarna),在挪威是泰勒马克(Telemark),在芬兰则是卡累利阿(Karelia)。或者把视野变换一下再来看的话,也可以说,被选作为野外博物馆的“景观”,才会被视为代表了国家的地方。
野外博物馆的设立及其对地方上的“景观”的选择都有民族主义在背后运作,这一点或许可以通过这一事实得到更好的证明。也就是,现实中的国境外侧的“景观”也得到了再现。比如,丹麦的野外博物馆(Frilandsmuseet)从开设时起,就把17世纪北方战争战败后被夺去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的斯科讷(Skåne)地方的家屋、第二次石勒苏益格战争中被普鲁士剥夺的南部石勒苏益格地方的家屋,移筑入馆内,作为丧失的国土“景观”来展示。这些民家和“景观”在丹麦的野外博物馆创设之时就已存在,直到现今也还在展出。
与万国博览会有着关联的野外博物馆,是一种通过有选择地对各地方的“景观”进行再现继而仿制出微型国土,实现“民族国家像”可视化的媒介。所谓“景观”的文化遗产化,也就是在这样的政治状况中生发出来的事项。
至此,我们已对野外博物馆诞生的政治背景进行了检视,它与万国博览会有着联结,并且是民族国家出于实现自己的国土可视化的目的而把各地方的“景观”集拢起来的产物。接下来,笔者尝试着在同时代的视觉文化背景中对其定位,并展开论述。
在此要留意以下两类研究。第一类研究认为,诞生于19世纪的铁道,使我们对于空间的认识产生了有史以来的巨大转变。第二类研究认为新的视觉体验通过博览会、博物馆、主题公园等展览形式来呈现,是为了让人们见到与自己日常生活不同的其他生活状态,因而也可以把近代交通方式的变化与把新的视觉体验作为文化来展示的学术及商业性机构进行关联,展开研究。
铁道不仅仅是一种能够实现以往交通工具不能做到的,使大量的人与物资在高速、短时间内进行长距离移动的技术,更是一种能使人类生出未曾有过的全新视觉体验的媒介。
由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在1780年制成的低压蒸汽装置经过改良后,1825年在英国的斯托克顿(Stockton)和达灵顿(Darlington)之间建成了世界上最初的商业铁道。19世纪前半叶,铁道的使用不仅推进了产业革命,还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旅行体验。以往的旅行,徒步的形式自不必说,骑在马上,或是乘坐马车,疲劳都与之相伴而行。但基于新兴的蒸汽装置的铁道旅行则把人从疲劳中解放了出来。在其法语词源中意含着“骨折”“劳动”“苦痛”的“travel”(旅行)一词,在借助蒸汽之力的铁道和蒸汽船相继出现之后,转变成了不见劳苦、享受愉悦的“tour”(观光)。
在此之前,陆上旅行都只能以步行的速度,再快也就是以马的速度来行进。在这样的速度之下,人们会融入环境中,并用五官去感受与体察当下的自然和人的生活。然而,铁道把旅行者隔离在运行于铁轨之上的密室中,使其只能通过窗户去触及世界,这就将视觉从五感中单独地切割出来,并放大了它的特权。在此,列车凭借着蒸汽之力实现了以往仅靠人、马之力无法企及的高速移动。眼前的事物,转瞬间就向着后方飞逝而去,失去了纵深的景物变得平面化,提供了展望全局的可能。借由这一新的视觉体验,不也就让人眼所见的车窗里的映像亦可被称为“景观”了吗?铁道让人们反复来回地接近或是远离自己生活和工作着的街道、农村、海村、渔村,列车以车窗的四角为基准,切取沿途的一片生活场景来作为“景观”,并让人在对比这些接连变化的“景观”中体验愉悦。
19世纪因铁道而新生的视觉体验,已成为今日之人的理所当然了,今人或许也就难以理解它在诞生之初为人们所带来的冲击和惊奇。根据沃尔夫冈·希弗尔布施(Wolfgang Schivelbusch)收录在《铁道之旅》(The Railway Journey)一书中当时人们留下的相关记载,19世纪中叶新闻记者兼评论家朱尔·克拉勒蒂(Jules Clarétie)曾这样写道:“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它(铁道)能够将整个法国都呈现出来,在你眼前展开的是无尽的全景,是一幅巨大而连续的、极富魅力又充满全新惊喜的画面。将风景的神韵展现给你看的铁道,犹如一位殿堂级的艺术家。它不问细节,只求生动的整体。它用画家般的技艺令你陶醉,而后又忽然停住,就那么简单地让你离开,去你想去的地方。”
铁道把世界变成了一幅“panorama”(意即“全景画”)。所谓“panorama”,是由希腊语的“pan”(意即“全部”)和“horama”(意即“景致”)这两个词源所构成的。18世纪末的英国画家罗伯特·巴克(Robert Barker)依据严密的透视图法照着圆形剧场的内壁作了一幅广角的情景画,由此开启了全景图画的创作。全景馆内可见到远方的风景和战争场面。而这些全景馆,却与铁道旅行的普及成反比地相对衰退下去。也就是说,原先人们把在馆内壁面上所描绘的情景当成一种全景,与之相对的,铁道的出现则让真实的情景反过来被全景化。
这一因铁道而生的崭新视觉体验,或许能在日本人所写的文章中获得更切身的体会。自1872年新桥—横滨铁道投入运行以来,日本就开始向全国推广铁道。虽然,明治时期日本铺设铁道的首要目的是促进产业发展和进行军事输送,但全国铁道网的建成以及江户时代铺设的道路也给人们带来了不同寻常的旅行体验。对日本民俗学的成立起着重要作用的柳田国男曾在《风景的成长》一文中这样写道:“火车可以让人见到预想之外的景色,对于此,已不会有人意识不到了吧。那恍如白丝带般的山路风情,连续不断地欣赏不同村落所带来的兴味,还有那些村落展现出来的自我装扮和被迫跟上时代而动作的样子,我们之所以能够静静地眺望着这般事物,皆源于‘火车之窗’的出现。或也可将这些称为不曾奢求的联结。那从未想要将其紧捉的小鸟,那不曾动念采撷食之的红色果实,这些让旅人们为之‘啊’地赞其美丽的场景,在弥次和喜多八的时代是不可多遇的。”
火车这一交通机械的速度产生了一种视觉体验。这种体验把日常生活从自我意识中剥离出来,并用客观的角度对之进行审视与比较。这一新的视觉体验,与观察并研究人们日常生活的民俗学的视线形成了共振。柳田国男还在《村与学童》一书中,取用透过火车窗户见到的“景观”作成合适的题材,促发孩子们去好好地观察事物。《村与学童》是一本面向在太平洋战争下为避难而从首都疏散逃往外地的孩子们而书写的读物,旨在提醒他们,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应该尽力去观察地方上的生活,并好好地进行思考。
假使透过火车的窗户去看的话,任谁都能很快明白过来,屋顶三角的角度会因前行所经之地的不同而不同。这大抵是与修葺屋顶的材料有着关联,因为同样都是草屋顶的话,哪怕在不同地域有着不同的倾斜度,也只是表现出些微差异而已。不过,换作板材屋顶的话,三角尖端发生的变换能够轻易地为肉眼所捕捉。假如乘坐中央线,山梨县的范围是从小仏的隧道开始到日野春和富士见的两个车站的中间那一段为止,行进途中肉眼所见的屋顶形状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那是因为东边的一部分都是用茅草修葺的屋顶,从西到西北边,越接近长野县的那部分地区,板材屋顶就越来越多了。
如果乘火车时观察,就会察觉到不同土地上的人家的屋顶形状也不一样。像这样乘坐火车将各地方的建筑物进行比较的视觉体验,可以说是给在野外博物馆里对各地方“景观”中的建筑物进行比较的体验做了铺垫。
总之,所谓野外博物馆,就是把映射在火车车窗里,由此为车窗所截取的“景观”重新集合在一处进行立体再现的设施。而“景观”先是被临时设置在万国博览会上,接着则在野外博物馆里成为常设。正如克拉勒蒂在书中所写,铁道“能够将整个法国都呈现出来,在你眼前展开的是无尽的全景”。野外博物馆则是在为参观者“上演”国土范围内各个地方上的“景观”,由此在其眼前展开全景。今和次郎在1930年去欧洲进行视察旅行时,关于野外博物馆曾这样说道:“在斯德哥尔摩的户外博物馆斯堪森里头,有一个区块收集并保存着这个国家的各个地方的旧的民家及其他建筑物。并且,正是在各建筑物的周围添置了各地的农田、牧场的情景,使得人在博物馆内徘徊却犹如在远方的土地上旅行一般。”野外博物馆就是一个能实现不坐火车但也能旅行全国,并体验到各个地方“景观”的设施。
北欧的民俗学研究得以推进并成立民俗博物馆,也就是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这段时期,而这也正是民族主义兴盛的时期,同时又是观光旅行的增长期。到1870年,北欧诸国的远距离铁道、蒸汽船航路、道路等修筑齐备,电信网和邮送体系也开始剧烈地扩张。得益于此,地方与地方、都市和地方、本国与外国之间的移动和交流飞跃式地增长。北欧诸国最初的观光协会也就成立于1870年前后。有历史学者这样写道:“从列车的窗户里、蒸汽船的甲板上,旅行者就能窥见到往昔的民俗文化依然鲜活着的样子。”在这样的时代中,为了使都市住民和外国观光客在都市里就能见到地方上的生活,因此诞生了野外博物馆这一游乐设施。
曾明确提及凭借机械速度而扩增的旅行与野外博物馆之间的共通性、共时性关系的,要数在战前的京城帝国大学教授人类学的学者秋叶隆。秋叶去英国留学时,于1924—1926年用了1年又10个月左右的时间在外国居住、旅行,他在这段时间内游历了夏威夷、美国本土和法国的民族学、人类学相关博物馆。此后,他将这些见闻以《博物馆巡礼》为题,在《民族》这本刊物上分四期进行了连载。其中有一段这样说道:“一般来说,去往外国,或者不仅限于外国,在国内各地方上,就可亲见各种各样的民俗。就算这种亲眼所见,常常是透过火车的车窗,目睹的也不乏兴味十足的事物。不过特意来到西洋,却选择在夜间乘坐火车的愚蠢之人也大有人在。尤其是那些难得选择了乘坐火车,却在车厢里睡大觉或是打扑克的人更是不可理喻。从火车车窗向外眺望的世界,就算称不上是一所大学校,至少也是一所大博物馆吧。在这个由神创造的大博物馆中旅行,逐步游览各具地方特色的民俗博物馆,对于我来说真是极为愉快的旅程。”
“从火车车窗向外眺望的世界,就算称不上是一所大学校,至少也是一所大博物馆吧。”这个比喻,正好指向作为一种观赏“景观”之媒介的野外博物馆和铁道之间的关联。
如果把野外博物馆文化视为在万国博览会上再现各国、各民族生活“景观”的展览往学术方向推进之后所形成的设施的话,那么往商业方向推进后形成的就是主题公园了。香川雅信参照希弗尔布施的《铁道之旅》一书,对在大正时期的博览会上给人带来全景式知觉体验的游乐设施和玩具展开论述时这样提醒道:“或许我们有必要好好地重新思考一下,为何经常会在游乐园、主题公园里放置‘儿童火车’。”比如,东京的迪士尼乐园里有一个名为“西部沿河铁道”(Western River Railroad)的游乐设施。奔走于19世纪后半叶美国西部开发时代的列车,不经意间闯入了恐龙生活的太古世界里。乘客相继眺望着鹿儿成群、未被开垦的草原,拓荒时代的火车站,美洲原住民的村落等“景观”。除此之外,迪士尼乐园还有坐小船围绕“亚马逊河”“尼罗河”“伊洛瓦底江”的丛林巡航项目,有坐船环绕世界一周的“这是个小世界”(伴随着《小小世界》这一乐曲会出现身着各国民俗服装的人偶映入眼帘)项目,甚至还有不少类似于环游《星球大战》中的宇宙,乘坐体验模拟星际旅行的游乐设施。

于1987年起在朝日电视台放映的《从车窗里看世界》(See the World by Train)这档电视节目,如其名所示,可以说是承接了19世纪铁道所生出的视觉体验这一谱系。它把在世界各处奔走的火车之车窗里所见的风景和车内的情状,停靠站的城市、街道、村庄的生活映像作为节目放送,仅是这样的映像放送就能获得众多观众——他们通过这样的节目获得了趣味,这种感受与通过观看野外博物馆、主题公园里所再现与展示的国内以及世界各地之“景观”时产生的有趣感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说明这二者在视觉文化史上是有所共通的。
把将“景观”作为文化遗产来保护的野外博物馆与主题公园以及它的游乐设施,或者和电视台纪行类节目摆在一起讨论,从文化遗产学或博物馆学的“严肃”立场来看,或许是要为之皱眉的。但若从视觉文化史的角度来看,野外博物馆的诞生毫无疑问与上述这些事物之间有着松散的联结。要说有什么基准能够将野外博物馆和这些事物区分开来,也不过就看是否为其增添些学术上的说法罢了。
承前文所述,在万国博览会主会场的室外场馆内,各宗主国展示殖民地的住民以及欧洲各国展示本国传统生活的行为,源自1867年召开的巴黎万国博览会。这也正是濒临垮台的德川幕府作为日本政府代表去参加的万国博览会,德川庆喜的弟弟德川昭武作为他的代理前往参加。涩泽荣一是德川昭武的随行人员之一,他出身于当今埼玉县血洗岛的一户富农之家,凭借经营蓝靛的才智崭露头角成为保皇志士,做过一桥家的家臣后又成为幕府的家臣。他在当时的旅欧日记《航西日记》中对室外场馆的样子进行了如下描述:
外部则是任由徜徉自得。每日暮时作一散步运动,方得一番细致游览。这一处内部略广,非一两日内可看罢。游园集萃地球之动植物,佐以博物学者之考证,可作将来讨论钻研之素材,促成营作农业之新法。宫殿亭榭堂塔家屋,万国俱异其风,外俭内奢,显各国旨趣殊异之风土民俗。增益学识之余,将万里缩于咫尺间又尽显五族相交之谊。


由此可知的是,室外场馆内展示了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以及动植物,而涩泽荣一对其做了彻底的观察。
在之后的明治时期里,涩泽荣一活用了当时在欧洲旅行中所见闻的近代金融、产业知识,设立了许多的银行和公司,后被称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而在设立和经营银行、公司的同时,涩泽荣一还着力于举办博览会。他担任了第三、第四、第五回“内国劝业博览会”的事务委员、评议员,“平和纪念东京博览会”的会长、“大礼纪念国产振兴东京博览会”的总裁,以及哥伦布世界博览会、巴黎万国博览会、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的评议员。
如此看来,涩泽荣一的孙子涩泽敬三,为了配合在1940年召开的作为日本最早的万国博览会的“纪元2600年纪念日本万国博览会”而提出开放附设日本最早具有全国规模的野外博物馆的“皇纪2600年纪念日本民族博物馆”一事,也是可以想见其历史因缘的。1924年,涩泽敬三停驻在横滨正金银行伦敦分店期间,曾去北欧旅行,参观了瑞典斯堪森、挪威民俗博物馆。1925年回国后,涩泽敬三把去英国之前就已在自家设立的阁楼博物馆朝着研究机构的方向进行了扩大。从乡土玩具的研究慢慢发展为民俗学、民族学的研究,在距离参观北欧民俗博物馆仅10年有余的1936年,他向文部大臣提议建立一个设有野外博物馆的“皇纪2600年纪念日本民族博物馆”。
话说回来,从本文的问题意识出发,笔者在重读涩泽敬三所主持的阁楼博物馆的调查、研究活动的资料时,察觉到这些调查、研究活动带有一种强烈的特质。即如前一节里所论及的,近代交通方式的变化和基于这样的变化而新生的视觉体验,是与这些调查、研究活动交织在一起的。他们做调查时是借助船或火车来移动。记录了如今已沉没在大坝底下的新潟县三面村山村生活的电影《越后三面行》(1933年),它的影像是从前往三面村的火车和车内的画面开始播放的。同行伙伴在车内瞌睡的样子被放映出来,高桥文太郎打着盹儿刚一睁开眼时的姿态被摄像机给拍下,还有他意识到后害羞地笑了起来的模样也被录入。这些画面不仅让人看到了涩泽敬三的玩笑与俏皮,同时也是在“上演”他们一行人从都市赶来,不断地换乘火车,在舟车劳顿中不由得在车上入睡的场景,以此来反映都市距离之远。而拍摄新潟县桑取谷的小正月仪式的电影《谷滨桑取谷》(1935年)的开头一幕,就好像《从车窗里看世界》那样,持续放映着在沿海岸线铺设的铁道上运行的列车窗外的风景。
此外还有刻意选择,利用乘坐火车、蒸汽船时可以对随行变换的画面进行比较、观察的手法来进行调查,将其视作一种认识各地的生活并对其进行分段考察的方法。这也就是后来被称为“迅疾调查”(rapid survey)且被柳田国男用于“水上大学”的调查方法。这是在朝鲜半岛的多岛海域诸岛、濑户内海盐饱诸岛、奄美群岛的萨南十岛等等海岛上进行生活调查时,由专攻各个领域研究的人逐岛短期停留进行连续调查时所使用的方法。朝鲜半岛的多岛海域调查,是在船中停留两晚花费三天,围绕七个岛展开的,盐饱诸岛的调查则在一个岛上最短停留四五十分钟,最长也不超过3小时。对于这种“迅疾调查”,河岗武春强调说它是以涩泽敬三青年时期的旅行经验为基础。涩泽敬三早在东京帝国大学就读期间就与友人坐帆船绕着濑户内海进行过巡航。此外,自1921年他就往返在英国和日本之间,有过船旅经验,还有在英国时去往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峡湾的经验。他还在1926年和石黑忠笃等人在出席台湾美国大会之后的归途中,顺道去了冲绳,从船上眺望着“路上之岛”并在鹿儿岛登陆。河岗称他为“不是那种待在船舱内的人,甲板旅客才是涩泽的特色”。
如果把视野放宽的话,可以把涩泽敬三他们的学问实践在以下背景中进行定位。也就是如野村典彦所说的,“作为一种爱好的旅行”和“民俗学”的诞生共同得益于铁道这一媒介/技术,且两者之间既存在交叉、混杂,又相互分离、芒果体育手机版独立。而我们或也可将这一发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系列行为还原到同时代的日本整体进程中去理解。正如前述,乡土玩具作为一种使人踏上兴趣之旅的促动装置,阁楼博物馆在最初就已对其展开了研究。在收录于自己六十岁纪念写真集《柏叶拾遗》的《旅谱》一文中,涩泽敬三将自幼年起的大半生所做的旅行进行了细致的记录。这样热爱旅行的涩泽敬三,同时也是一位研究者,他倾力于在其所有旅行的终点——日本,设立和瑞典斯堪森一样的野外博物馆的这一行为,从视觉文化史的角度来看也是有其必然性的。
在涩泽敬三等人的努力下,把全国各地的民家集合起来进行“景观”再现的野外博物馆的建设构想,以小规模的形式得到了部分实现。1939年,在东京市郊外保谷的日本民族学会附属民族学博物馆里,由武藏野民家迁筑而来的绘马堂被建了起来。不过,“皇纪2600年纪念日本民族博物馆”还未能设立就迎来了日本战败期。战后,基于1950年起实施的《文化财保护法》,“民俗资料”被加入文化财保护之列,因而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国家文化财保护委员会以及与之相关的学会中设立国立民俗博物馆的呼声一度十分高涨。当时所构想的国立民俗博物馆也有附设野外博物馆(进行全国性规模的民家迁建)的计划,但最终没能实现。民族学博物馆也在1963年闭馆了。
将全国各地的民家迁建过来进行“景观”再现并建设成为野外博物馆的事,最有可能得到实现的时期是1981年成立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之时。在1975年通过的《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基本构想》中,有这样的表述:“把室外展览作为常设展览,计划适当配置与室内展览主题有所关联的民家、石造物等。特别是将有特色的民家建筑物(包括其周围的环境和内部的器具)统合为一个展示物,以能够推进对其生活全貌作出理解的方式来策划展览。”此外,同是1975年通过的《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设施整备计划》中,有把“邻接佐仓中学的地区”作为“武家屋敷、合掌造民家、大和栋民家等全国有名建筑物的室外展览场”这样的表述。
然而,就算在基本构想里做了这样的描述,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里也未能设立野外博物馆。对于这点,有一说是因为“展览”的概念在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成立之前与之后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在20世纪70年代,“作为发布研究成果的展览”这一所谓把抽象的研究成果直接输送给参观者的“展览”概念的转变,使得在野外博物馆内作趣味性参与、模拟体验的那类展览被刻意回避。
除此之外,也可列举类似于预算不足、馆内工作人员对此毫不关心等等这类简单的理由,不过笔者在此仍想尝试从新的角度去理解。也就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文化遗产的保存方式由通过在野外博物馆里再现地方风貌进行保存的方式转变为在原地原封不动地进行保存、活用的方式。在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的基本构想被决定采用的1975年,《文化财保护法》也被修正,新设了保护“传统的建造物群”的制度。与一直以来建筑物只被作为单独存在的保护理念不同,这一制度是从那些被称作城下町、宿场町、港町之类的历史性街区以及农渔村落里选定对象,对其采取集合式的整体性保护。此外,1975年的修正还把“民俗资料”这一名称更换成“民俗文化财”,并且随之设立了把信仰仪礼、民俗艺能等指定为“无形民俗文化财”来进行保护的制度。总之,自1975年起,不是在野外博物馆内进行迁建与再现的保护制度,而是在原地直接进行保护的这一制度逐渐得到完善。
颇有意思的是,与这一将地方住民的生活作为文化财进行直接保护的法律举措同时并行的是,这一时期通向各地方的铁道旅行也得到了普及与扩大。20世纪70年代起,日本国有铁路不断开展其所举办的“探索日本”(Discover Japan)的宣传活动。自1964年的东海道新干线投入使用以来,日本国有铁路输送能力不断上涨,至1970年已能将6000余万人运送至大阪的万国博览会会场。而有着这等能力的日本国有铁路,又借此推动营业额的上涨。“探索日本”的宣传活动,并不只是指向特定几处观光地,而是计划把日本全国作为旅行目的地。它的广告语是:“让我们通过旅行去发现日本丰富的自然、美丽的历史传统和细腻的人情,并深入地去感受吧!”更进一步到了团体旅行得以普遍化的年代,它也积极地创设出单人旅行、夫妇旅行这类项目。
综合整理如上论述,19世纪后期,欧洲在博览会和博物馆内将民家迁建过来进行“景观”再现,并依托其上演节日、年中仪礼及民俗艺能。到了100年后的20世纪后期,则变成在原地原封不动地保存、活用。野外博物馆的形成要归功于兴起于19世纪的铁道的建设速度,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由于铁道高速化的不断加剧,比起迁建并再现地方上的“景观”,在地的生活直接就可转变成为野外博物馆。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日本,人们无须去野外博物馆看再现的“景观”来感受旅行的氛围,而是可以直接去旅行目的地看就在原地得到保护的“景观”。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的室外展览计划未能开展的原因,也可以在视觉文化史上得到这样的解释。
放眼世界,20世纪70年代,有乔治·亨利·里维埃(Georges Henri Rivière)提倡的在原地对生活、环境进行原模原样保护的“生态博物馆”运动。随着野外博物馆概念范围的“外延化”,野外本身成了博物馆的现象并不为日本所独有。在日本,名为野外博物馆的这一形态至今未能扎根,进行全国规模的民家迁建来实现“景观”再现的国立野外博物馆一直未能设立。而在地方自治体所设立的博物馆中,就算是把民家迁建进馆,以建筑史上的、艺术上的价值为中心对地方生活进行再现的例子也在少数。几乎未经历过野外博物馆的阶段,就直接对其概念进行了外延化(对野外本身进行博物馆化),这也导致1975年《文化财保护法》修正时创设“传统的建造物群”和“无形民俗文化财”保护制度的行为,被视作非常突兀的现象。但若不把视野局限于日本而是放宽一些来看的线世纪的欧洲伴随着交通手段的变化而新生的视觉体验、观光旅行得到扩增,在博览会、野外博物馆内的“景观”再现以及20世纪后期的野外博物馆的概念外延化这些趋势中,我们就也可理解这一现象了。并且,或许也无须多言的是,野外博物馆的概念外延化,并不只停留于建筑物、信仰仪礼、民俗艺能等生活的一部分,更意味着将住民生活着的环境统括进来作为文化遗产对其进行彻底的保护,也即催生出了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进入大众视野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及《文化财保护法》中“文化景观”这一条文。
本文回溯了“景观”是如何作为文化遗产被保护起来的历史过程。“景观”的文化遗产化作为法律制度被确立起来虽是产生于近些年的现象,然而从视觉文化史的角度出发,可以将其放在新生于19世纪的视觉体验的这一延长线上来考虑。
并且,被作为文化遗产来保护的“景观”变成观光地这一事,若寻其历史由来,虽然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并无相悖之处,但也可察觉到此事并非源自近年。所谓“景观”的文化遗产化是伴随着借由近代的机械之力让身体去旅行成为可能的视觉体验之出现而生,并得以展开的一种现象。此外,民俗学也是与“景观”的文化遗产化产生于同一社会状况的学问。瑞士的民俗学者巴尔布罗·克莱因(Barbro Klein)在回顾瑞士自19世纪后期至今的保护民俗的历史时这样说道:“自由市场经济之下,文化保护、娱乐和获取金钱,这三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这种共生关系,早在出现像哈则流士那样的博物馆创设者的时代就可见其端倪,并且随时代推移,产生了哈则流士和他的同伴们做梦都没想到的结果。”
然而,在野外博物馆里再现“景观”与被《文化财保护法》指定或依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被登录为遗产而在原地原封不动保存、活用,这二者之间有一个决定性差异,即“景观”的重要构成部分是那些在家屋里生活、在田间劳作的真正的居民,而人们在野外博物馆所看到的不过是使用薪资雇用志愿者所进行的表演。与之相对,依据《文化财保护法》和《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地域住民实际生活着的场所被保护起来,也因此是把真实生活的场景展示出来。关于这一点,我们想以被纳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白川乡、五箇山的合掌造聚落”的白川村荻町合掌造的成排家屋为例,来做一些思考。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白川乡、五箇山的合掌造聚落”本身并不是作为“文化景观”被登录的,但正如下文所示,近些年把“景观”保护起来的意向在不断增强。
作为“文化景观”被保护起来的地域里的住民们,为了满足观光客想要看到“原风景”的欲求,将自己的生活伪装成“一如从前的生活”。黑田乃生对这种自我表演的方式进行了认可并推荐这种做法。黑田自己作为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参与了白川村荻町的文化遗产化过程,并对其进行了如下的提案:
为了在早已算不上是农村的白川村荻町保护尚处农村时所产生的文化的景观,在某种程度上做出“表演农村”的决断是有必要的。关于生活着的人成为展出物的这一点,人们经常会围绕着虚实问题展开议论或责难,但对于居住在其中的人来说,有必要将地方发展成更好的观光地来维持自己的生活,而且只要他们担负着将遗产的价值传递出去的责任,就只能居于其中去积极地摸索办法。或许有些武断,但不妨这样去想:他们出于前述目的,而在展示上做出努力,在传递技术上做出精进的话,对于来访者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在荻町,围绕如何保护景观这一问题有着活跃的讨论,随着议论的不断扩大,做出了这样一些举措:花钱耕种已经休耕的农田,赞助用传统素材或是用不太显眼的塑料薄膜制作防雪栅栏。以这样的方式把被保护的“景观”和蜂拥而至的观光客想要看到的“原风景”进行结合,就是所谓的“博物馆式”视点。
引用之际,要附加说明的是,最后所说的“‘博物馆式’视点”里的“博物馆”是指能够调动五官进行趣味学习的自然科学类博物馆。然而,从本文考察的野外博物馆的诞生历程来看,黑田的这则提案无疑是在说住民生活的野外博物馆化。更确切地说,从即便科学技术得到飞速发展(并且还会持续发展下去),还要伪装出一如从前的“原风景”这一点上来看,就不能说它是带有学术目的(通过对生活进行展示以期理解生活之变迁)来进行展示的博物馆,而只能说是为了迎合来访者的主题公园罢了。正如黑田自己所说:“也可把荻町视作以‘传统村落’为主题的盛大的主题公园。”
不过仔细想想的话,只是当地住民们的风景的“景观”为何会被作为“日本人”的“原风景”登录成为具有民族价值的文化遗产呢?并且作为“原风景”的“景观”为何会与观光旅行结合起来呢?由于前文已有叙述,无意再次对其进行批判性的论述了。不过,在此不得不指出随着把观光客想要看的“景观”作为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这一举措而生出的两个问题。
第一,应该被原模原样保护起来的“景观”本身是在发生变化的。在白川村荻町进行长期调查的才津祐美子指出,合掌造的家屋并置的“景观”自1995年被登录为世界遗产以来,不仅因为面向观光客的土特产店和饮食店的增加而发生“恶化”,还因为在所谓的大学里的研究者的专家们的指导之下,以“修景”的名义对景观进行“改善”,包括街灯设计的变化、电线的铺设以及把柏油铺设的马路变成和土地颜色接近的工程之类的改造,而不断发生着剧变。
第二,地域住民们曝露在观光客的视线之下,即使是身处现代也要在伪装成“一如从前”的“原风景”中那样生活,从而产生生活的不自由和压力感。关于此点,才津也提到在持续进行着“修景”的状态中生活的住民感到了困惑和愤怒,并且才津也指出,必须从在当地生活着的人们的视角来考虑文化遗产的保护方式。此外,藤涌豪也在参观记中记录了自己在访问合掌造村落时,因为完全见不到当地居民的实际生活场景而感到了违和。接着在更进一步的观察之下,他记录了那些住民们避开观光客的视线的生活场景,比如稻子在没有观光客的大清早被人收割,傍晚放学路上的中小学生,在路上谈笑风生的女性,等等。
然而,即便是指出了“景观”成为文化遗产后在当地产生的今日之种种问题,我们也没法迅速找到解决办法。根本性的解决办法要属撤销作为“文化景观”的指定与登录,或者更进一步,删除《文化财保护法》的“文化景观”这一条文,退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样的方法,从理论上来讲也不是不可行,但在现实层面上要实现无疑是困难的。我们要想从19世纪的机械速度所产生的视觉体验之后果中抽离出来并不容易,毕竟一旦这样说出口,也就陷入到那无法后退的狭路中去了。
现如今,住民所生活着的环境被作为“景观”保护起来,而以观光这片“景观”为目的,不断有人前来造访。那么,在这些将“景观”作为文化遗产保护起来的地方,研究者与研究机构又是以怎样的形式与之产生关联的呢?笔者想要打一个比方,那些想看“景观”的人们,好比是急着“从列车上下来”的人,而那些对着“景观”只是做一番“啊,好美啊”的感叹的人,是心中有一扇“车窗”的人。柳田国男、涩泽敬三,不只从车窗(或甲板)向外眺望风景,还从列车(或船)上走下来,与人们的生活相接触,去调查、思考如何才能让生活变得更好。柳田国男对于铁道所开拓的新的视觉体验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他自己也享受透过车窗去观看并借此来观察生活的过程。然而,作为一个调查者,仅仅从车窗进行观看是不够的。他被要求从站台上下来做调查,不是用铁道搬运身体时的机械速度,而是用步行时的身体速度去观察当地、去聆听民声。
涩泽敬三和阁楼博物馆的同伴们,从交通工具上走下来,去拍摄影像、照片,记笔记的同时也收集器物,包括那些被称作“民具”的物品。“民具”这一概念不只是一个学术标本,其中还浸入了对使用着这些物的人们的生活的钦佩之情。这是与同样关注“物”,但只是将其作为审美对象来看待的柳宗悦所提倡的“民艺”完全不同的。今和次郎在分别与涩泽敬三和柳宗悦去岩手县的荒泽村旅行之后,对于两者的态度进行了如下叙述:
第二次来到这个村子是出于农林省的政策需要,为了对极度贫苦的农家施以援手,让他们能够有些小钱周转,也就是为处理关于副业的问题来此进行视察。当时参加的有柳宗悦、滨田庄司、河合宽治郎等人。这一行人看待物的方式,皆是沉醉于鉴赏之中,对农民的实际生活方式之类的事情则是无视的。是一种沉湎于鉴赏之中的态度。全然未把农民的生活与学问、社会福祉之类的事情关联起来。
涩泽敬三一行人来此的目的,是把那些从事着农工商业、被视作常民的人们过去一直使用但现在全都用不上了的器物,以及原模原样反映着过往生活的衣食住之类保存下来并流传给后世。他们仅是出于此种意图来着眼于物,且是以一种冷静的态度来做这样的事的。
“民艺”的“耽于鉴赏”之眼与只想把“景观”作为单纯美景来看待,这二者在不对当地人的生活进行反省这一点上,是共通的。如果有过反省的话,就也不会想要把“一如从前”的“景观”强塞给当地住民。如果是出于把观光客想看的“原风景”保护起来的意图的话,在野外博物馆的场地之内对其进行再现也已足够。
不仅把“景观”作为一个切入口,还要借此广泛地、深入地去对生活进行观察,朝着思索生活形态的方向前进。在此过程中,研究者参与进来,试图活用博物馆这一机构朝这一方向去进行引导。也因此,在这个像被热病冲昏了头一样的欲求着美丽“景观”的现代社会,产生了一个走投无路般的迂回性选择,就是把“景观”作为文化遗产保护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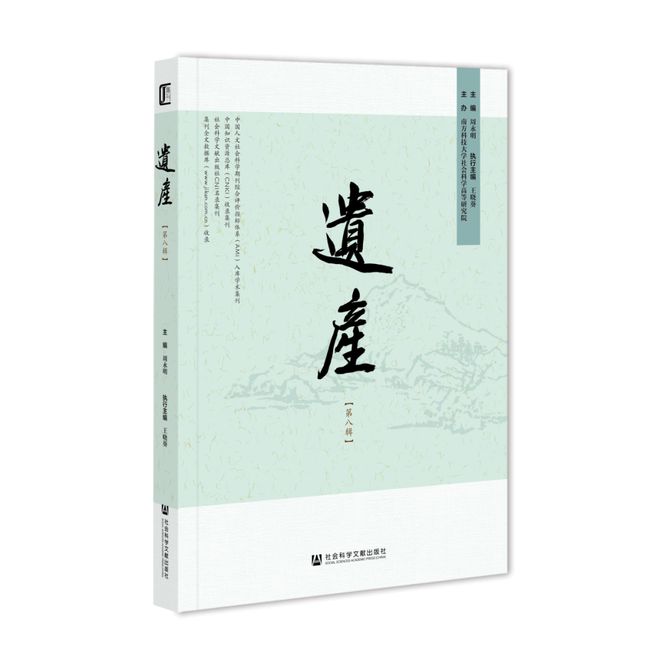
《遗产》是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办的学术集刊。遗产丰富多彩,包罗万象。本刊倡导尊重人类遗产的多样性和整体性,鼓励从广义的“大遗产”概念出发,对遗产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践研究。跨学科是遗产研究最显著的特性,本刊欢迎运用新方法、新技术进行研究,鼓励学术创新和跨学科交流。遗产研究既有理论思辨,也有经验分析。本刊倡导立足当下,关注当代社会对人类历史和价值的不断解释和建构。遗产为全人类所共有。本刊关注本土经验,也主张国际视野,介绍各国遗产研究的动态,刊发海外遗产研究成果,鼓励比较遗产研究,展示人类遗产多样化的共性和个性。
· 遗产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超越“无人在场的文化遗产”悖论——文化遗产人类学之议题与视野(上篇)[日]饭田卓/文陈亦欣/译阮云星/译、校两种文化际遇处的文化遗产课题——文化遗产人类学之议题与视野(下篇)[日]饭田卓/文陈亦欣/译阮云星/译、校春节成为韩国法定节假日的过程及原因探析董贺源纽约中央公园和奥姆斯泰德的景观设计思想遗产熊庠楠声音遗产的建构:有声档案背景下的知识积累[德]约翰内斯·米斯克/文袁邈桐/译
· 遗产研究的多学科视角 ·景观的文化遗产化——观光旅行、博览会、博物馆的19-20世纪[日]丸山泰明/文余玮/译中国:一种基本方法李安宅/文吉佐阿牛/译边境城市民俗学:以下关朝鲜裔居民为例[日]岛村恭则/文周萌/译“民艺”:如何对待物?[日]竹中均/文[日]马场彩加/译作为文物的桑基鱼塘保护研究任远李琛张稣源
· 遗产与信仰 ·色、相与音声:认知佛教艺术遗产邓启耀民间信仰的非遗转向——基于北川大禹祭祀仪式的调查研究刘超汉藏圆融:青海瞿昙寺营建历史与文化传递陈祎韬
· 遗产与文学 ·《勺园祓禊图》跋文研究——附跋文印章图像及释读转写张红扬韩湘子宝卷的版本系统及其相关问题李婷宜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上午还在收钱,下午就失联!老板“卷款跑路”?涉及资金约12亿!办公室人去楼空,警方已介入...
常德一男子称遭家暴申请人身保护令,法院驳回:岳父母和小姨子不属家庭成员
热搜!鲁迅孙子称自己时间“90%刷短视频,10%看书”!网友:太线全渠道禁售!英伟达:国内用户RTX 4080/70/60系列正常买
映泰推出适用于英特尔酷睿 i7-14700K 处理器的 Silver 系列主板
4090买不到!RTX 4080、4070 Ti最快本月清空库存:英伟达马上送新品
海外网友热议T1夺冠:Faker是LPL最大克星!theshy打得像鬼一样
WBG全员释然安慰小虎!教练透露上路BP做出牺牲,TheShy感慨老了
父亲在家长会上坦言儿子是学渣,“但我依然相信他会有个美好的未来”父亲发言结束后响起热烈掌声